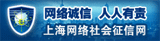|
||
通讯员 干晔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天色将明未明的时候,77岁的王时明做了一个梦。
天色将明未明的时候,77岁的王时明做了一个梦。
他似乎又回到少年时代,站在祖父养蜂的院子里。和煦的阳光下,一片嗡嗡的蜜蜂声汇织成一片温软的云层,令他情不自禁走近。祖父打开一瓶中国蜂酿的蜜,洁白如雪、一股浓郁的芳香扑鼻而来。他把手指伸进蜂蜜罐直接舀来吃。蜂蜜顺着手指流入嘴中,甜蜜的感觉立即浓浓地包裹了舌头,就如同洞悉了世间万物法则一般美好。
他伸手想再去开蜂箱,这才猛然醒了。嘴边依稀还留着儿时最幸福的感官体验。但是起床一看,窗外已经大亮。
新的一天来临了。而老人的心,已经跟着蜜蜂振动的翅膀,飞向了窗外的天地。
在松江车墩,老人的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养蜂人的俱乐部。他在这些永不放弃的小家伙身上看到了勤奋和活力,也为养蜜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忧心忡忡。他说,他要把这份“甜蜜的事业”继续下去,以饲养的方式,更以科研的方式。
不怕蜂蜇,追寻最美的甜味
王时明有时觉得,有一根看不见的红线,一头拴在蜜蜂身上,一头拴在他身上。不然为什么蜜蜂一振翅、一生病,他的心总会被拽得一跳一跳。
他想这根线,或许是祖父拴上的吧。祖父就是个养蜂人,家里养了10多箱中国蜂,每年都能收到两大桶蜂蜜。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令人垂涎的宝贝。但尽管贪吃,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忍受蜂蜇。当时饲养中国蜂的蜂箱是没有巢框的旧式蜂箱,巢脾不能移动。在收蜜时只能毁脾取蜜,这样,每收一次蜜,蜜蜂就要重造一次巢。因此,每个花期只能收一次蜜,不仅产量低,而且也会阻碍蜂群的发展。
十五六岁时,还在松江一中念初二的王时明发现饲养意大利蜂用的是一种活框式的蜂箱,巢脾可随意取出,收蜜时可重复使用,一个花期就可多次收蜜,产量高又不影响蜂群的繁殖。“而且这样的蜂箱可以更方便检查、观察蜜蜂,我当时就和祖父商量着也用活框式蜂箱来饲养中国蜂。这在当时整个上海郊区可谓是首创。”
就这样,还是少年的王时明戴上简易的面罩一头扎进蜜蜂堆里。由于被蜜蜂蜇过太多次,王时明的体内有了抗体,现在蜜蜂蜇一下就像被蚊子咬一样,都不会肿起来。但他也遭遇过不小的心痛。“中国蜂会感染一种中蜂囊状幼虫病,这相当于蜂的癌症。”上世纪60年代初,王时明养了十多年的十几箱中国蜂就是因为这个至今都未能彻底解决的病而全军覆没了。当时的打击难以形容。
从那时起,王时明就没再养中国蜂了。后来从一个朋友处买来一箱意大利蜂,重新开始培育繁殖,从一箱发展到20多箱。但是,在他的味觉记忆中最好吃的蜂蜜始终还是中国蜂的蜜,“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蜂蜜”。
观察昆虫,审视人生的价值
现在很多年轻人有“网瘾”,王时明说自己是有“蜂瘾”。
多年养蜂,王时明从不贩蜜盈利。酿出的蜂蜜除了留给自家食用,一般就是馈赠亲友。但是比起蜂蜜,他对蜜蜂更感兴趣。
养蜂的时候,为了不妨碍周边居民,他把蜂箱放在较远的竹林里。每天他总要去看他的蜜蜂,常常一看就忘了时间,看得投入,连吃饭也经常忘记,那时候老伴经常要去摆蜂箱的地方喊他回家吃饭,他却津津有味:“在小小的蜂箱里,蜜蜂们工作繁杂而多样,喂幼虫、建蜂巢、服侍蜂王、打扫蜂箱、外出采蜜、安全保卫等,它们各司其职,工作井井有条,这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群体,充满自信和活力。”
他曾经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观察蜜蜂的 “婚礼”。观察蜂王出生后在蜂箱里发生的种种故事。从最初“王室斗争、消灭异己”的惊险,到蜂王“出巢试飞”时的忐忑不安,到被成群结队的雄蜂“追求”时的情景,直至最后终于“洞房花烛”的喜悦。他还看到过蜜蜂智斗癞蛤蟆、对决大马蜂的过程。当看着蜜蜂怎么群策群力赶走前来偷蜜的蚂蚁时,他也会像孩子一样一边看一边叫好加油。
说起这些,满头白发的王时明像少年一样兴致勃勃。他说,观察蜂箱里发生的事情,就像在俯视自己的生活。除了乐趣,也有触动和震撼。“你知道吗,一只蜜蜂穷其一生只能酿出一勺半的蜂蜜。”接下来的一串数字更让人震撼:要制造出一斤蜂蜜,需要5300只蜜蜂去采集花蜜。一罐蜂蜜意味着蜜蜂要在花朵和蜂巢间往返8万次,飞行5.5万英里,采集200多万朵花…… “它们总有难以想象的耐心对付各种困难,从不言放弃。”和蜜蜂相处久了,这些小小的生物在他看来就如同老朋友一样。他舍不得它们,也放心不下它们。
上世纪,爱好写作的王时明曾是一家报社的工农兵通讯员,一度在当时报社所在的外滩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难得的工作机会。但每当海关大楼的钟声“当当”响起,他似乎总是听到蜂群的“嗡嗡”声在召唤他。难解“相思之苦”的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松江,在家乡的华阳镇中心学校担任老师、一直做到校长,再也没有离开过心爱的蜂群。
每当看到这些小家伙不辞辛劳地采蜜归来,老爷子就感到他和大自然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总让他想到脚下的土地、花朵和稻田,感到一种脚踏实地的力量。
情牵未来,永不停步的钻研
蜜蜂们有时工作起来“不要命”,有时还春寒料峭,它们就迫不及待地出发采蜜了。但往往来不及回来,就在外面冻僵了,一只只掉在蜂箱前。那时候王时明就会去一只只捡起来,很仔细不落下一只,每一箱前常常要捡起一大碗,再小心翼翼地放回蜂箱。他真是爱它们。
但光有爱还远远不够,一个优秀的养蜂人还得掌握相当多的科学知识,才有资格照顾它们的一生。
从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探索蜜蜂的科学管理、科学饲养,从改良蜂箱,到研究蜜蜂的防病治病、培育良种等。他还是《蜜蜂杂志》的特约通讯员,经常通过这个平台和全国各地的蜂友们交流养蜂经验。2003年,他完成了《蜜蜂和蜜蜂精神》的文稿,记录了近百个关于蜜蜂生活的小故事,每一个都是他亲眼观察到的。
“但是,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这些花的开谢时间都提前了差不多10天左右。电子产品的电波干扰、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蜜源植物遭破坏等这些外部因素正在不断影响到蜜蜂的生存。今年四五月份,连着好几天多雨,温度又低。蜜蜂连油菜蜜也没吃到,几名外地来松江摆蜂箱的养蜂人几乎是哭着回去的。”对于蜜蜂的未来,他心存着一丝忧虑。“在人类所利用的1300多种植物当中,有1000多种需要蜜蜂授粉。爱因斯坦曾预言,如果蜜蜂消失了,那么人类的生存时间可能只有4年左右。”对此包括王时明在内,许多养蜂人都相信这绝非耸人听闻。
几年前王世明因病住院,因为担心父亲年事渐高身体会吃不消,孩子们瞒着他把20多箱蜜蜂送给了一位南汇养蜂人。可他还是闲不住,出院后一有空就去南汇看看自己的 “宝贝孩子”,即便待在家里,也整天伏案撰写着与蜜蜂有关的科研文章。他喜欢那熟悉的 “嗡嗡”声那是蜜蜂所唱的一首关于辛勤劳动的歌,也成了融入王时明生活的永恒旋律。